梅赛德斯奔驰始终保持开拓创新,一直致力于打造梦幻汽车。借助 DRIVE PILOT 自动驾驶系统,梅赛德斯奔驰汽车正在将创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一些驾驶条件下,驾驶员可以放开方向盘,在旅途中尽享舒适与安全,仿佛置身于未来科幻世界!曾经好几代人都梦想着驾驶梅赛德斯奔驰,但是现在,这辆车会驾驶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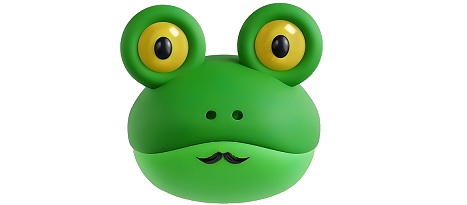
投稿、社交、聊天就来51蛙吖蛙元宇宙
梅赛德斯奔驰始终保持开拓创新,一直致力于打造梦幻汽车。借助 DRIVE PILOT 自动驾驶系统,梅赛德斯奔驰汽车正在将创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一些驾驶条件下,驾驶员可以放开方向盘,在旅途中尽享舒适与安全,仿佛置身于未来科幻世界!曾经好几代人都梦想着驾驶梅赛德斯奔驰,但是现在,这辆车会驾驶你。

在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的前一个月,创作者来到了这座「浪漫之都」,使用 Sony A7IV 相机拍摄了这支短片。他参观了卢浮宫、凯旋门,站在埃菲尔铁塔上俯瞰巴黎的全景,去塞纳河畔感受巴黎左岸的艺术气息,巴黎的一切,都像是一幅精美的油画一样,充满着浪漫和诗意。 From John X


有一个实验似乎还没有人提过,昨天无意中看到的,顺手写下来。
伊利诺伊的玉米遗传实验,从 1896 年开始,今天仍然在持续。
1896 年,农学家、化学家 Cyril G. Hopkins 在伊利诺伊农业实验站收获了 163 颗同种的玉米,这 163 颗玉米被分为 4 组:
1,24 根蛋白质含量最高的玉米
2,12 根蛋白质含量最低的玉米
3,24 根含油量最高的玉米
4,12 根含油量最低的玉米。
这 4 组玉米被分开种植,防止相互传粉,一根玉米在一块地里种一行,最高的一组种在中间。
第一年后,四组玉米都收获了,Hopkins 将结果发表在 1899 年的《Improvement i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corn kernel》中


可以看到高蛋白玉米(含量 12.54%)种植出了蛋白含量 11.1%的玉米,低蛋白玉米(含量 9.03%)种出了蛋白含量 10.55%的玉米,两者相差 0.55%。
当然,实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每一年,都将重复第一年的做法,从高蛋白 / 油的产出里面取 24 颗最高的,从低蛋白 / 油的产出里面取 12 颗最低的,继续种。
1900 年后,伊利诺伊玉米实验的负责人换成了 L. H. Smith,他们在 1908 年发表了实验的第二篇论文《Ten generations of corn breeding》,并公布了结果:

十年过去,高蛋白和低蛋白的差异已经达到了 5.62%,高蛋白组的含量上升到 14%以上,低蛋白组含量已经低于 9%。
1921 年后,负责人又换成 C. M. Woodworth,他们在 1929 年发表了论文《The mean and variability as affected by continuous selection for composition in corn》,公布了蛋白含量和含油量的差异:

蛋白和油的含量差异已经超过 8%。
如果说,伊利诺伊玉米实验一开始试验的目的只是想要看不断分开选种是否会造成子代的差异越来越大,那么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现在的实验已经有了下一个目的——完全通过选种的方式,使得蛋白质含量和含油量上升,这个上升会有上限吗?从前 30 代来看,两者的上升似乎都是线性的,并没有上限存在。
1951 年,伊利诺伊玉米实验的负责人又换成了 E.R. Leng,他们在 1952 年发表了论文《Fifty generations of selection for oil and protein in corn》,讲述了 50 代之后的情况:

看起来,含油量和蛋白质含量的线性上升并没有停止,且蛋白质含量的下降也是几乎线性的。含油量的下降则趋缓——毕竟含油量不能低于 0。
到了这里,伊利诺伊实验想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从高蛋白 / 含油组里开始选择那些蛋白 / 含油最低的玉米,同时从低蛋白 / 含油组里开始选择那些蛋白 / 含油最高的玉米,反向选育,然后不断重复,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个实验从 1947 年开始,1960 年时达到了 13 代,1962 年发表的论文《Results of long-term selection for chemical composition in maize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evaluating breeding systems》公布了该结果:


反向选育组的走向很有意思。虽然在之前已经经过了近 50 代的选育,无论是含油量还是蛋白质含量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从这些组别经过了仅仅 13 代的反向选育之后,之前的积累的优势就已经消失近半。比如在蛋白质组,反向高蛋白组和反向低蛋白组之间的差别和 20 代时已经差不多。
1966 年后,J. W. Dudley 接替了伊利诺伊玉米遗传实验,他们又在反向高油组里面进行了分叉,进行了一个「回旋」(Switchback),意思是在那些选了 47 代高油有选了 7 代低油的玉米里面再选 16 代高油玉米……这个玉米真的给折腾得够呛呢。
小组在 1974 年的《Seventy Generations of Selection for Oil and Protein Concentration in the Maize Kernel》发表了下列结果:


从这里我们又能看到,在含油量这一块,「回旋组」重新上升的速度还是挺快的;而在蛋白质含量上,反向高蛋白组的下降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仅仅 20 代后,之前 47 代的优势就全部消失了。
用两句话来重复这两个现象,对含油量来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对蛋白质来说,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2004 年,Stephen P. Moose 已经成为伊利诺伊玉米实验新的负责人,他们发表了论文《Maize selection passes the century mark: a unique resource for 21st century genomics》,总结了一个世纪以来的这一场玉米试验。

从这两张图看,蛋白质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还是在持续,从左图看,50 代后反向高蛋白组和经过了 100 年选育的低蛋白组已经几乎没有差别,把之前 50 代的优势完全抵消了;而 50 代后的反向低蛋白组到高蛋白组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含油量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也颇为有趣,「回旋」组已经基本赶上了高油组,弥补了 7 代的差异。而反向高油组和反向低油组也才刚刚碰面。看起来,对含油量来说,用选种带来上升和下降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两张图和百年前差不多的一个趋势——无论是蛋白质含量还是含油量,他们的上升仍然是几乎线性的,还没有看到显著的停止,在含油量的上升上尤其如此。这可能意味着玉米的含油量和蛋白质含量,尤其是前者,还远未被接近。
在最近几十年,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玉米遗传实验已经没有那么受欢迎了。同时我们也有更多更合适的物种来做实验,比如其他的答案里有提到的大肠杆菌实验,进行了三十多年,已经有 6 万代了,出现了很多奇妙的特性。伊利诺伊玉米实验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基因上的差异,比如实验的最近一篇论文发表在 2019 年 7 月——没错,就是上个月——他们研究了高蛋白组和低蛋白组由于 RNA 的不同而在「持绿性」上产生的差异并进而由于光合作用带来的产量差异。
总之,伊利诺伊玉米遗传实验仍然在继续。100 年前,Cyril G. Hopkins 大概完全不会想到他的实验还能有那么多玩法,期待在未来的 100 年,他们还能从中发现更多有趣的东西。
虽然是很简单的选种实验,但想来却十分神奇。差不多的一批玉米,分开来种,按标准选育,一个世纪以来更换了数位实验室负责人,观察了短短的一百年。
就是这一百年,已经让一批相似玉米的子女们出现了天壤之别。含油量高的,超过 20%,含油量低的,已经无法检出。

如上图所示,高蛋白组颗颗呈现圆形,而低蛋白组的颗粒则呈现长条形,在外观上也已经出现了差异。一百代,似乎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差异。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代又何足挂齿?
根据 2014 年发表在 Nature Genetics 上的论文《Inferring human population size and separation history from multiple genome sequences》,用分子钟计算基因变化速率,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共祖出现在 8000 年前,按照 20 年一代的算法,已经过了 400 代,相当于伊利诺伊玉米实验的代数重复了 4 次;中国人和墨西哥人的共祖出现在 2 万年前,相当于 1000 代,也就是伊利诺伊玉米实验的代数重复了 10 次。

再把目光放远一点,人类和黑猩猩的共祖出现在 600 万年前,就算 20 年一代,也有了 30 万代。
想象一下,600 万年前的一只猿类,她育有两个子女,其中一个是当前所有人类的祖先,而另一个是当前所有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祖先,而这相当于伊利诺伊玉米实验的代数重复了 3000 次。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进化不也正是大自然的一场大型实验吗?会不会有「反向」、「回旋」等控制因素被人类自己施加在身上呢?光是想一想,就觉得是一件非常带(kě)感(pà)的事情呢。

如果不维护,任其锈蚀的话,很难撑得过一个世纪。


本来只准备宣扬一下法国国威,用个 20 年给大家开开眼到 1909 年就拆掉将地皮还给巴黎市政府用作他用的,结果没想到这一落成就屹立了一个多世纪。
埃菲尔铁塔所用的一共 18038 块铁片的厚度不是均匀的,像主要承重结构部分里的铁片,厚度就会达到 10-12 毫米,次要的或者连接部分的厚度大概在 6-12 毫米之间,如果在完全不维护的情况下每年的腐蚀在 0.1 到 0.2 毫米之间,很难撑过百年。
尤其是巴黎的气候条件,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天更是降水充沛,雾气较重,空气湿润,就会加速铁的氧化与腐蚀。再者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又是全法国工业最发达、人口最集中的区域,工业活动的污染与酸雨又会加重腐蚀,总之,腐蚀速度会进一步加快。
一座铁塔的寿命不是说看每个部件,从头到脚完全腐蚀掉才会倒塌。而是那些关键部位腐蚀掉,结构出现问题,哪天刮一阵狂风,可能铁塔就被拦腰截断了。
所以铁塔每七年都会重新刷漆一次,防止锈蚀以避免结构出现损害。从 1889 年 3 月 31 日竣工以来,铁塔至少被重新粉刷过 19 次,每一次粉刷都会用掉 60 吨的油漆。
这里说一个小故事:铁塔一开始是通体刷“威尼斯红”漆,后来 1889 年世博会又在底部和中部加了一层棕红色,使铁塔从头到脚呈现一种由浅入深的渐变效果,更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1892 年又涂了一身的“赭色”,再到 1900 年世博会,铁塔底部涂上了橙色,渐变至顶部变成了明黄色,成了一座“黄塔”,之后到 1954 年前都是棕黄色为主,在之后又变成了棕红色,一直到今天。


铁塔的保养真的很重要,当初埃菲尔铁塔修好后很快就震惊了全球,一向和法国佬不对付的英国佬马上也开始修铁塔,要和法国一决高下。
除了布莱克浦塔很快在 1894 年竣工后,但高度仅只有巴黎铁塔一半高。新的更高的塔已经在利物浦附近的新布赖顿开工了:

新布莱顿塔 1897 年 7 月开工,1898 年到 1900 年间完工对外开放,173 米高,成为当时全英格兰最高建筑也是全球除巴黎铁塔外第二高建筑,四部高速电梯 90 秒就可以到达塔顶俯瞰整个利物浦城与海景,每小时可运送 2000 人。开放第一年就吸引了 50 万游客,虽然比不上埃菲尔铁塔,但是也算是成功了。
开业后 14 年,一战爆发,1914 年塔就被关闭了,关闭的四年里因缺乏维护,铁塔生锈,于是战争一结束就被宣告要拆除(尽管引起了争议是因为四年的锈蚀可能并没有严重到威胁塔的支撑结构还可以稍微修复一下),但最终还是于 1919 年完全拆除并将金属卖给了废品回收站(战争期间政府还打起了这个铁塔的主意希望向铁塔所有者购买这个塔的金属以支援战争,但被业主拒绝)。

写这个的意义是铁塔不维护的话,锈蚀速度和严重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按照当时的科技发展如果建成后不管不顾,可能现在巴黎的天际线早已没了铁塔。
当然真的哪天法国没钱维护了,铁塔塌了不在了,欢迎各国朋友来中国参观埃菲尔铁塔,高仿版简约版抽象版应有尽有:
比如深圳版埃菲尔铁塔:

杭州版埃菲尔铁塔:


澳门版埃菲尔铁塔:

昆明版埃菲尔铁塔:

烟台版埃菲尔铁塔:

上海版埃菲尔铁塔:


作为一名纺织品化学工程师,我就从纺织材料这个角度来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全篇干货没废话,先说下我个人的 3 个结论
1)衣服看起来出汗明显≠速干效果差,反而可能更好
2)日标的速干衣标准更适合剧烈运动出汗场景
3)樊振东是真的爱出汗体质
一:速干衣为什么比常规的衣服更加容易干燥?
很多消费者都会吐槽涤纶、尼龙这类化学纤维做的衣服穿起来闷热不透气,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涤纶、尼龙是运动速干衣的主流材料
在问题开始前,有个核心知识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那就是大众所说的“面料透气”是个非常复杂指标,不是面料孔隙多穿上去透气(直接测试透气性其实是防风指标)。
穿着透气不闷汗的本质,其实是让面料尽可能的吸收皮肤上的汗水,只要皮肤表面干爽你就会觉得穿着透气我们日常觉得棉 T 吸汗透气,是因为棉花的公定回潮率有 8.5%(100g 棉花能吸收空气中 8.5g 的水蒸气),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饼干受潮变软”的这个过程。

在日常休闲穿搭过程中,人体皮肤分泌的汗气并不是很多,棉花自身的吸水效果足够把皮肤上的汗水吸走,那自然就觉得很干爽了。
但是在剧烈运动大量出汗的情况下,擅长吸潮的棉就麻烦了,会阻碍汗水的继续挥发,就像在梅雨天的南方,即便是在晴天也很难避免饼干受潮变软。
所以速干衣选用的材料都是本身不擅长吸水的,例如涤纶的公定回潮率只有 0.4%,基本上完全不吸水。看到这很多朋友可能就疑问满满“材料本身不吸水那我还怎么吸汗?”。
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就有个你随时都能见到的物件,它的材料本身就一点都不吸水,但是做出的东西吸水性还特别好,那就是“发泡海绵”。放入水中立马吸的饱满,但稍微一拧就又干的很彻底。

因为这个吸水过程不是来自于材料本身,而是材料的自身结构,比表面积大毛细作用强

水都是吸附在材料的最表面,并没有深入材料内部,所以这种吸水也叫做“自由水”;与之相反的就是棉毛巾了,放入水中也能吸的饱满,但是无论使用多么大的劲去拧干,总还是会湿湿的,因为有一部分水钻入了材料内部,所以叫做“结合水”

所以,速干衣的开发本质,就是尽可能的降低结合水“选用不擅长吸水的材料”,增强自由水“提高材料表面的吸水效果”
二:速干衣的生产原理
想找到不擅长吸水的材料很容易,涤纶(聚酯纤维)、尼龙(聚酰胺纤维),这些非常常见。于是面料工程师开发的思路都是从如何“提高材料表面的吸水效果”这个思路入手
1)把纤维材料的结构从圆形变为很多沟槽的形状(提高比表面积)
常见的化纤涤纶大多都是圆形,因为最好纺丝加工,但要做速干衣,就得用点形状特殊的涤纶。例如十字形、毛毛虫等形状

这样能让材料的表面有更大的比表面积,才容易吸更多的汗以及更大的蒸发面积。

2)使用聚酯聚醚类的吸湿排汗剂
不过刚才说的还是最理想的情况下,真用到了这种异形截面纱线做成的面料后就发现,它的吸湿扩散效果也并不是很理想。
于是还要用“聚酯聚醚类的吸湿排汗剂”,这个化学物质一端有聚酯可以融进涤纶内部,聚醚的那一段又有很好的吸水效果,所以能让涤纶的表面很容易吸附汗水,从而让汗水扩散出更大的蒸发面积。

3)单向导湿技术
皮肤上分泌的汗水,被面料内层吸收走,然后汗水再传递到面料最表面蒸发。

正是因为有“汗水扩散梯度”的原因存在,所以好的速干衣还要想办法尽可能的把汗水逼到面料最外层。于是更加少见的单向导湿技术就出现了,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速干衣贴身层织入丙纶,因为丙纶有很强的疏水效果;
其次就是在贴身层印花“疏水剂”让内层拒水。万变不离其宗,本质都是为了让速干衣靠近空气一侧的面料更容易吸汗,皮肤贴身层不容易吸,这样穿着起来汗干的更快,因为汗水都在第一时间从皮肤上转移到和空气接触的外侧,而且贴身层还相对干爽不易粘身子。

所以这样的技术能把汗水尽快的逼出到面料表面,自然汗水看起来也更加明显了,但这并不代表实际穿着就有汗水粘身的问题。
三:日本 JIS 速干衣的测试标准通过难度更大
莫穿的是优衣库,如果执行的速干标准为日标 JIS 的话,那速干率效果确实很高

这是因为国标和日标的速干衣的检测方法不同

国标速干衣测试中的干燥速率,是在面料上滴上一滴水,然后称量 1 个小时后这滴水干燥了多少。
日标速干衣的测试就严苛很多了,是把衣服面料完全浸泡满水,然后让衣服先滴水到没有额外水滴下落,然后再测试 1 个小时后干燥了多少。
所以从测试方法上来看,国内的速干衣测试本身就更倾向于休闲速干,出汗量并不是很大。日标的检测测试则是极限速干,体现的是在剧烈运动大量出汗时的速干效果。
四:樊振东的出汗量本身就很大
说到底不同人身体素质差异真的很大,樊振东在各个比赛时都有大量的出汗情况,速干衣只是辅助装备。